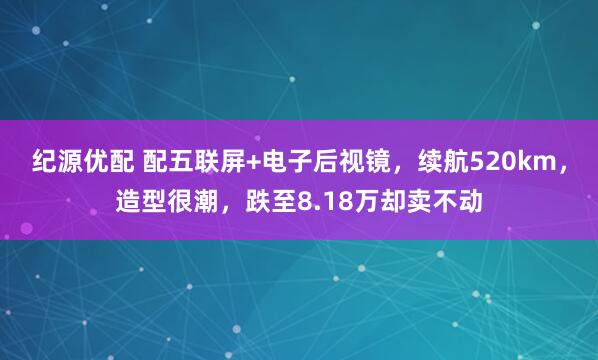2025年6月16日,洪湖龚家后墩水域的千亩荷田迎来盛放期。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在湖风中起伏如翻涌的绿色浪潮股查查,粉白的荷花星星点点缀满其间。这片壮阔的荷莲盛景,源自去年种下的藕种,如今已扎根生长为连绵不绝的生机绿洲。(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弦 倪娜 通讯员 李斌
“水生植被大面积消亡后,恢复起来有多难?”
去年今日,洪湖龚家后墩仍是一片“白水”——水面无根、风过无痕,像一块被擦净的镜子,映得出天空。62岁的曾令炽把藕种抱上船时,心里没底:真能长出荷田来?
 2025年3月26日,村民们在湖中栽下藕种。(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2025年3月26日,村民们在湖中栽下藕种。(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曾令炽,祖辈都是洪湖渔民,以湖为生。洪湖生态危机爆发后,曾令炽带着上岸渔民下湖种草。他们智斗群鱼、大雁,驱赶野鸭、蓝藻,只为守护能净化水质的藕种平安长大。
据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统计,经多部门共同努力,今年底洪湖的水生植被覆盖率有望达30%。眼下,此前在洪湖大面积消亡的水生植物,正艰难且缓慢地逐渐恢复。
 在洪湖龚家后墩水域,密密麻麻的荷田中,不计其数的荷花点缀其间。(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在洪湖龚家后墩水域,密密麻麻的荷田中,不计其数的荷花点缀其间。(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扛过洪水,老荷田“长大”300亩
7月初,记者跟随曾令炽进入湖区。发动机轰鸣,小船飞快航行在洪湖“高速公路”上,这是新开挖的航道。进入湖区,定位软件失效,渔民的大脑就是最好的GPS。下“高速公路”,水路渐窄,前方就是龚家后墩,一片密密麻麻的荷田映入眼帘股查查,湖风吹来,荷叶翻涌成浪,荷花点缀其间。
水面越来越浅,堂弟曾令平跳下船推着小船靠岸,曾令炽默契地拴紧绳子,将船固定。钻进荷花间,曾令平一下子不见了踪影,几分钟后,手上多了一把莲蓬。“今年的头茬莲蓬,还嫩得很。”曾令炽望着一人多高的荷花荷叶,黝黑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拨开荷叶,曾令炽回忆说,去年种下900亩藕种,为了防鱼吃,他们利用湖泥,筑起围埂,围埂内放低水位。看着大雁飞走了,大家才赶紧将藕种种下,因为大雁会打洞吃嫩藕。万幸扛过了去年夏天的洪水,今年还扩大到了1200亩。
“这就算是‘长大成人’了,能抗击湖里的风浪了!”曾令炽感慨万千。
不仅“长大”300亩,荷田水下也有虾须草、苦草等沉水植物长了出来。“荷叶下的湖水清亮得很,这是‘猪耳朵’。”曾令平伸手从水中捞起一把碧绿的水草,因叶片圆肥且有一缺口,被渔民唤做“猪耳朵”。芡实宽大的叶片上,正躺着4枚棕色光滑的鸟蛋,它们是有着“凌波仙子”之称的水雉刚诞下的宝宝。
 曾令炽(右)和曾令平查看荷花长势。(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曾令炽(右)和曾令平查看荷花长势。(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新荷田遇新烦恼:没防住野鸭偷吃
去年种下的荷田旁,正是今年春天实施的272亩野莲扩繁项目,眼下只有少部分荷叶露出水面。“万万没想到,今年没防住野鸭!”曾令炽摇着头说,因洪湖大部分区域植被尚未恢复,野鸭无处觅食,刚种下的藕种就成了它们的美食。
为护藕种,曾令炽和曾令平连续18天,半夜拿着手电筒,一遍又一遍驱赶野鸭。野鸭还没赶完,他们发现湖里长起了一部分蓝藻。为了修复水生植被,今年以来洪湖持续保持较低水位,连日高温导致蓝藻出现。在湖北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湿地修复中心主任罗东平的指导下,曾令炽和曾令平扛来抽水泵,用高压水枪冲散蓝藻。
“一旦蓝藻覆盖整个水面,水生植物就难以生长了。”罗东平说,洪湖本地红莲生命力顽强,根茎泅水长度可达3米,只要第一年存活率超过30%,第二年就会自我繁衍,扩大水体覆盖面积。
想着眼下正在经历的汛期,曾令炽也充满了担忧:“刚长出来的荷叶最怕水位居高不下,希望今年我们也能扛过这轮汛期。”
 曾令炽(右)和曾令平在查看去年栽种的荷花长势。(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曾令炽(右)和曾令平在查看去年栽种的荷花长势。(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有水草,洪湖水质才有改善希望
“目前来看,洪湖水面广、吹程长、风浪大,导致水体浊度较高,沉水植被尚不具备良好的恢复条件。”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院研究员厉恩华说,只有沉水植物大面积恢复,才能大幅提高湖水自净能力,但在当前情况下,恢复挺水、浮叶等水生植物,能为沉水植物生长创造条件。
眼下,洪湖水面内约有2万亩水生植被恢复项目,但大水面恢复较难,因此各项目进展不一。“我们正在摸索,在人为努力下,创造一个挺水、浮叶、沉水植物共生的生态场景。”罗东平说。
船回码头,夕阳把荷叶剪成金箔。老曾剥开莲蓬,莲子还嫩,甜里带涩——像洪湖此刻的味道。
“明年,这片能不能到1500亩?”老曾眯眼望湖,水面荡起细碎的银光。风把荷香推上岸,也把他的问句吹得很远。
灯已点亮,只需时间,把光铺成海。
 在洪湖龚家后墩水域股查查,密密麻麻的荷田中,不计其数的荷花点缀其间。(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在洪湖龚家后墩水域股查查,密密麻麻的荷田中,不计其数的荷花点缀其间。(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嘉正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